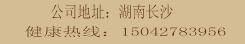武忠弼教授是享誉中外的著名学者。自年代初期起的20余年间,因种种机缘,使我与武老晚年生涯有交集。本文从个人亲历的见闻,追忆武老生前的往事片段。文内所附照片,多选自《病理学家武忠弼教授画传》。
某些涉及校史的内容,由于距今年代久远且并非本人亲历,特节录武老生前(年)所撰《百年沧桑母校情——亲历同济医学院校史鳞爪》(简称《自述》)一文中的相关资料,作为补充。
心系同济武老于年考入国立同济大学附中,年以第一名成绩被同济大学医学院录取,亲历了母校历史变迁的诸多重大事件(如抗战中西迁四川、抗战胜利后重归上海、解放后由沪迁汉、改革开放后重启与德国的传统联系、几经周折的校名更替、本世纪初高校合并等),堪称同济校史的“活化石”。武老与同济风雨同舟七十余载,其个人命运始终与母校紧密相连,故对母校具有超越一般人的深厚感情。
武老在同济任教逾60年,历任教务处副处长(-)、副院长(-4)。自80年代初起武老任校方的对外联系代表,9年10月退休直至其病逝,一直被聘医院(协和、同济)的外事顾问。武老为母校的发展鞠躬尽瘁,同济医学院百年校庆(年5月)之际,老人已因病住院,仍在病榻上打电话、发邀请、写邮件,协助学校邀请余位德国贵宾出席纪念庆典。
武老对母校爱之深,凡事关母校发展和建设,常在不同场合直抒己见,或向领导和职能部门提出各种建议,即使有时因此而遭冷遇或误解,亦不改初心,始终如一。大约是年,我们随团访问德国ESSEN大学,当地夏季白昼很长,晚饭后我陪同武老去旅店附近的Gruga公园散步。闲聊中谈及医学院建设的相关事宜,笔者“斗胆”进言,认为其提出的某些看法及建议未必完全符合实际,或并非尽合时宜。闻此言,武老当时沉思良久,未作正面回答。数月后在另一场合(已不记得话题的缘起),武老谈及中共早期领导人瞿秋白就义前所撰《我的自白——多余的话》中的一句引语(出自《诗经》):“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当时我不由私下揣测,这可能正是武老屡发“逆耳之言”时的心境。
武老在其《自述》中曾作如下表白:“不时有人出于好心劝我罢手,但为母校发展,我毫无悔意。道理很简单,是母校把我从十几岁的孩子培养到今天这个状态,一个人万万不可忘本。我爱母校胜过一切,愿为母校发展贡献终生。我曾对当年的校长薛德麟表态:我愿为母校同济的发展,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并非豪言壮语,而是出自内心的表述。”
德国情结作为老一辈同济人,武老对德国有特殊的感情。
武老曾于年赴原东德洪堡大学进修3个月,此外并无长期出国经历。但是,其德文口语及写作水平,在医学院教师中鲜有人出其右,令人佩服之至。武老记忆力超群,许多生僻的德文名词、地名、德国人姓名,都过目不忘,并熟知德国历史及现状。此等功底,是其得心应手地开展对德学术交流及民间外交的“本钱和底气”。
年裘、武二位教授率团访德,重启我校与德国的传统联系。其后我校陆续与十余所德国大学建立了校际合作,先后派遣数百名教师和临床医生赴德国进修和学习。以今天的眼光来看,这些似乎不属“丰功伟绩”。但是,在文革结束后的相当一段时间内,人们的思想仍受旧时清规戒律的束缚,开展对外交流不仅遭遇种种阻力,甚至还须承担某些风险。前辈们得风气之先,解放思想,不计个人得失,为促进我校国际交流、人才培养和学科建设而勇往直前。平心而论,武老堪称其中的杰出代表,功不可没!
武老倾心参与和推进中德合作凡30年。在对德交流的不同场合,武老谈笑风生、出口成章,德文典故和成语信手拈来,妙语连珠。许多德国友人评价,武老的德文水平不亚于受过高等教育的德国本土人。因此,武老广受德国医学界(甚至政界)的尊敬和推崇,有极高的知名度,可谓“无人不识君”。
鉴于武老为促进中德交流所做出的杰出贡献,5年他与裘老荣获德国政府颁发的德国大十字勋章(下左图),并于年荣获德国总统颁发的星级大十字勋章。武老是同时获此两项殊荣的唯一中国人。年5月,德国总理默克尔访华,武老应邀专程赴京,在德国驻华使馆获接见并合影(下右图)。此外,武老被包括海德堡大学在内的多所德国大学授予荣誉博士头衔,并获多项奖励。
顺便提及一件往事。德国人比较刻板,传统上极为重视头衔和地位。年武老随团访德结束后,由法兰克福乘机回国。当时,全团人员的行李集中托运,同时顺序办理登机卡,轮到武老,发现其不慎将护照装入托运行李中,此时已由转送带运走。经再三协商,机场工作人员重新找回行李,当面开箱取出护照,同时发现了行李箱中的星级大十字勋章和证书。立刻,机场工作人员的脸色和态度大变,热情地与武老攀谈,并极为恭敬地为其办理了登机手续。
智者风范终其一生,武老将弘扬同济文化和传承同济精神视为己任。医学院有许多学生社团,凡邀请武老参加活动,只要时间允许,他都来者不拒。武老的讲座成为广受学生欢迎的耀眼品牌。
本人曾有机会旁听武老的人文讲座。是晚,可容纳人的大教室座无虚席,连走道也站满听众。讲座持续2个小时,武老始终站立在讲台,中间未曾休息,对同济的校史娓娓道来、如数家珍。在场的年轻学子全神贯注、鸦雀无声。精彩之处,课堂内不时爆发热烈的掌声。本人从教多年,可以真切感受到现场讲者和听者产生思想共鸣及心灵交汇时的氛围。武老本人也陶醉其中,这可能是作为一名教师梦寐以求的最高境界。
武老去世后,同济校园学生会随即发出告示,当天取消一切娱乐活动及无关的社团活动,同济学子们还自发举行了各种悼念活动。在校方为武老举行遗体告别仪式的当日,数千学生自发列队参加悼念,校园主干道两旁,到处悬挂和张贴着学生们自制的纸质白花及撰写的挽联、悼词。
武老平时衣着得体,无论在对内或对外的各种场合,均谈吐高雅、举止得当。武老自尊自重,去世前数年,已是年逾八旬的老者,凡赴国内外公干,生活完全自理,连行李箱都坚持由自己提,上下楼梯经常一步跨两个台阶,谢绝旁人搀扶和帮助。即使罹患恶疾后住院治疗,他仍然坚持每天自己梳洗、剃须,在外人面前不失尊严。
(年出访柏林时所摄,是武老第66次、也是最后一次赴德,时年87岁)
随性而为80高龄的武老始终葆有年轻人的心态。他多才多艺,常自得其乐,且时有出人意料的随性之举。
武老待人宽厚,曾自嘲“没大没小、没老没少”。日常交往中,对他人某些似乎有冒犯之意的言辞,也从不计较。笔者应属武老的晚辈(年龄相差23岁),但自80年代初相识始(彼时本人才届不惑之年),武老言必称“老龚”。时隔多年,武老呼我“老龚”时的音容笑貌,犹在眼前。
直至老年,武老不拒烟酒。其夫人杨宜娣教授曾多次拜托外事处的同事,对武老进行“监督”,但收效甚微。武老嗜好冰激凌。年中期,武老随团去德国ESSEN大学公干,在该校进修的同济教师设晚宴招待其一行。餐后,在一众好事者的“怂恿”下,武老“豪情满怀”,创造一次进食1公升冰激凌的历史记录。
武老喜好美食,且食欲始终旺盛。中德医学会创办的“临床肿瘤学杂志”,医院肿瘤科主任于世英教授任常务编委。同济校区附近的华美达饭店底层曾开设一家正宗的法式西餐厅,为感谢老教授们对杂志的支持,每年年末于教授均在该处专门设宴,受邀者为裘、武二老和吴在德校长,笔者也敬陪末座。全套西餐包括前菜、汤、主菜、甜点、咖啡、水果。武老每次均照单全收、彻底“消灭”,且意犹未尽。饱食之后,同座者有时“不怀好意”地提议再加一份冰激凌,往往正中武老下怀。从旁观察,武老进餐完全是一个享受的过程,令人不由感佩老人生命力的旺盛以及对生活的热爱。
裘武之谊提及武老,必然与裘老有联系。二老相识、相交60余年,共同为同济医学院建设、发展而倾注大量心血。许多情况下(如同济医学院、中德医学会、德国医学杂志、学报外文版等),武老均担任裘老的副职,但二者堪称君子之交、珠联璧合,即使工作中难免出现意见分歧和争执,彼此也从无芥蒂。裘老91岁(5年)生日之际,武老赋诗一首祝寿,道尽二老的深厚情谊。
法祖仁兄91华诞
人云七十古来稀,
尔今八十小弟弟;
吾兄九秩又出头,
来日方长建奇迹。
此生有幸结知交,
夫复何求名与利;
承邀贱弟同偕老,
愿与共历风霜雨。
(左图:4年在医学院迎春座谈会上。右图:二老在云南石林论剑比武)
裘武二老均享高寿,对母校的感情至死不渝,为母校的发展奉献终生,可谓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在他们生前,笔者曾当面戏言:“二老患有裘武综合征,临床表现为年届九旬,仍然思维敏捷、精神抖擞、壮心不已。我等晚辈,不敢奢望如此高寿,更勿论身体如此健康、斗志如此昂扬、工作如此玩命。”二老闻之,不以为忤,反而捧腹大笑。
武老晚年听力明显下降,对外界的反应略显迟钝。但是,话题一旦涉及“同济”、“病理”和“德国”,他立即应对如常,尤其对裘老“挑衅”的话语更是反应灵敏。为此,旁人戏称其患“选择性耳聋”。
裘武二老心灵相通,但平素喜“文斗”,往往成为聚会时在座者期盼的“余兴”。针对裘老“取笑”自己耳聋,武老扬言“本人听力不好,但是真货,不像某人自夸眼明,却是赝品(指裘因白内障而植入人工晶体)”。武老常嘲讽“外科医生什么都敢干,什么都不懂”,裘老则反击“病理科医生什么都敢干、什么都懂,可惜太晚了(指病理解剖处理的是死人)”。裘老“贬低”武老一生都给自己“拎包”,武老则笑言:“缺了我这个“跟班”,有的人(指裘)什么事也办不成。”
年初武老罹患癌症,裘老亲自主持会诊,确定治疗方案,术中亲临手术室坐镇,术后不时赴病房探视。当年10月底武老已病重,其意识尚清醒,但自知来日无多,最后告别时二老在病床边相拥而泣,在场者无不动容。
乘鹤西去武老健康状况一直良好,直至八旬高龄,仍头脑清楚、精力充沛、身手矫健。因此,医院求诊或体检。5年前后,武老出现顽固性皮肤瘙痒,经久不愈,但其未以为然。院系领导曾专门为其调整办公室,以避免接触不明的致敏原,未见效。
年春节过后,学院外事处即开始私下张罗,拟邀约几位老同事于3月19日举行宴会,祝贺武老88岁生日(米寿)。没能料到的是,当年3月初武老突发肠梗阻,诊断为结肠癌,并立即手术,医院。武老住院期间,校、院领导十分重视,医院及主管医生竭尽全力救治,无奈现代医学回天乏术。年11月8日,武老永远告别相伴终身的同济校园和热枕挚爱的莘莘学子。
附:改革开放之初的武忠弼教授
(摘录自武老所撰《百年沧桑母校情——亲历同济医学院校史鳞爪》)
前言促使我(武教授本人——摘录者注)撰写此文的缘起有二:一是出于对母校的感情和热爱,感到有义务和责任让后来者真切了解母校的历史沿革,以发扬“同济精神”,共同为母校未来建设和发展而奋斗;二是关心同济的校内外人士一再嘱咐,鼓励我将母校历史沿革记录下来,供领导、校友和同学们参考。由于个人经历和记忆所及有限,相关史实难免有片面甚至错误之处,望予指正。
恢复对德联系
历史上,我校与德国科技界有着传统的合作关系,也是我校特色之一。但自二战结束后,与德国的联系及合作基本断绝。70年代末,邓小平重新主持工作并提出“改革开放”的方针政策,重建对德联系成为当时校领导集体的共识。
年秋,德国斯普林格出版社在武汉医学院举办图书展,时任德国大使馆文化参赞Theodor女士专程来汉出席开幕式。我校组织12位教授与其座谈,且全部说德语,使其大为惊讶。我遂向她解释了母校历史和由沪迁汉的经过。Theodor说自己曾多方寻找同济医学院“下落”,现在却无意中取得联系,她激动地引用一句中文谚语“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并表示德国驻华使馆愿协助我校恢复与德国的联系。
我们立即向卫生部汇报此事,并获得支持。鉴于我国当时与东德均属“社会主义阵营”,若使用官方身份可能令东德产生误解和不快,乃决定以卫生部“器官移植考察团”名义出访西德,由裘法祖和武忠弼任正副团长,团员为夏穗生、王巽义和刘恭植。行前向卫生部汇报,时任部领导强调,我们此行的任务仅限于考察器官移植,不得讨论合作问题,不得访问西柏林(属“敏感地区”),更不可签署任何协议。
(自左至右:夏穗生、武忠弼、裘法祖、刘公植、王巽义)
我们一行经巴黎转机去德国。先期到达德国的裘夫人赶赴波恩迎接,但不知我们所乘具体航班,经向我驻德使馆询问,使馆竟不敢相告,也不敢请她进使馆休息,以致裘夫人不得不在使馆附近的马路上等候多时。其后使馆王参赞获知此事,曾专程来旅馆表示歉意。可见,彼时人们的思想远未真正解放。
在德期间,德方负责提供住宿,另每天每人给予80马克零用。为节约外汇,裘夫人自告奋勇到附近餐馆打听价目,最后我们一行6人站在一个小食铺外的街边,吃廉价快餐充饥。(回国后,我们将节余的外币全部上缴卫生部。)
此行我们先后访问波恩、海德堡、汉诺威、美因兹、慕尼黑等地大学。裘教授于-年曾在慕尼黑留学和工作,也是他结识和追求裘夫人的旧地。时任慕尼黑大学医学院院长Spann提及,当年裘教授曾为他做过阑尾切除术。慕尼黑市议会在市政大厅为我们举行欢迎晚宴,议长致词时表示:“裘夫人在中国多年,为中德友谊做了很多工作,为有利于两国今后的交流,慕尼黑市愿意恢复其德国国籍。”裘夫人旋即致答词,表示在中国生活得很好,工作无问题,当面婉绝了议长的建议。
在慕尼黑期间,接我驻德大使电话,称医院获悉我们正在德国考察,特邀请我们去该院访问,并提供机票及一切费用。鉴于离京前卫生部领导已有指示,我们不敢擅自行动。我急中生智,试探大使应如何处理为妥。大使当即回答:华国锋主席此时正应邀访德,你们若拒绝邀请,可能造成不良影响。闻此言令人喜出望外,我随即表态全团愿意应邀去柏林访问。
年10月,我们大胆违背了出国前卫生部的指示,由法兰克福直飞西柏林,受到医院Hierholzer教授热情接待。在出访即将结束的告别宴会上,他拿出一份长达数页的会谈纪要,请我们审阅并签字。这一“突然袭击”令人措手不及。我匆匆阅读后,认为其中内容均对我方有利(如接受我校青年医生去该院进修学习;无偿向我方提供实验室设备等)。随即,裘教授和我以考察团正副团长的名义,斗胆在会谈纪要上签了名。
我们回京后即如实向卫生部汇报,强调该纪要完全对我有利,故未经请示而签了名。当时部领导未予批评,似乎已默认。但过了一段时间,卫生部向全国通报此事,批评我们违背指示,擅自与德方签署协议,应引以为戒。
通过此次访问,为我校与德国的合作奠定了基础。其后,我校于年11月12日与海德堡大学签订了第一个对德合作协议。自此,我校与德国的传统联系得以重启。
创建实验医学研究中心
年初,我校领导班子改组,由张泽生任党委书记,裘法祖任院长,魏西、文历阳和我分任副院长(分工负责教学、科研和外事)。新班子合作愉快,并就大力推进和加强学院建设取得共识,决定筹建实验医学研究中心,供全校开展实验研究之用。
彼时,正值德国科技部部长Hauck应邀访华,其由德国大众汽车公司基金会秘书长Borst陪同,将专访上海同济大学,并赠款万马克支持该校筹建固体物理实验室。获悉此信息,裘教授和我决定力争,也从该基金会获得赞助。但是,湖北省科委认为我校未获德方邀请,且国家科委也并未就此作出安排,故不宜前往。其后经再三申请,科委才同意我们以私人名义约见Hauck部长和Borst秘书长。
我们抵达上海后,获同济大学校长李国豪(裘老赴德留学时的先后同学)热情欢迎,且邀请我们参与接待。在德国驻华大使Wickert夫妇协助下,我们得以会见Hauck部长。同时,Borst秘书长同意接受邀请来我校访问。在赴武汉的飞机上,我提出德方能否也向我校赠款万马克,资助建立实验医学研究中心(对外称为“保尔·艾尔利希研究所”)。他当即表态可考虑赞助80万马克。我引用中国的谚语说“一碗水要端平”,何况我校是同济大学的前身。Borst遂表示愿为此事提供帮助。
Borst回德后不久即来信告知,大众汽车基金会董事会已讨论通过我们的申请,决定向我校赠款万马克,用于资助实验医学研究中心购置仪器设备。其后,Borst博士再次专程来汉,向我校递交了赠款证书。在此背景下,我校向卫生部和省政府申请建楼拨款获准。3年10月,六层楼的大厦及附设的学术报告厅建成,大众汽车基金会项目负责人Pentschuk专程来汉出席揭幕式,并赠送1万马克用于为该中心购置图书。
医院始末——功败垂成
我们这一届医学院领导的“施政方针”之一是,为学校筹建一所医院。德国法兰克福“医院公司”是具有国际声誉的大公司,他们希望在中国这个潜在的大市场占有一席之地。我们与该公司几经磋商和交涉,对方愿以低息贷款方式为我校新建医院。我们将此事视为学校发展的重要机遇,随即开始进行筹备。
张泽生书记、裘教授和我专程拜访了时任武汉市委书记黎智,获其大力支持,同意在汉阳十里铺提供0亩土地,此事也获湖北省政府支持。我校随即按照德方要求,提供了建院所需的大量信息资料。公司随即派遣设计人员专程来汉,对选址的地质和环境进行实地考察,并启动设计工作。
建院相关情况向卫生部汇报后,我于年6月陪同卫生部代表团赴德实地考察。2年10月,裘教授、魏西副院长和我再次出访德国,通过与医院公司会谈,经反复协商,对方将建筑预算(包括设备)由最初的8.3亿马克(约合4亿人民币)降至4亿马克。
我们回国后分别向陈丕显书记和卫生部作了汇报。陈表示省里大力支持,并立即与卫生部领导电话联系,希望由部、省、市医院给予帮助。卫生部二位副部长专门接见我们并听取汇报,允诺将由卫生部和湖北省共同上报中央,争取立项。德国医院公司也在最短时间内完成了设计方案。
根据当时的国务院规定,投资额超过万元的建设项目,均须上报国家计委审批方能立项。时任国家计委主任S认为该项目耗费过大,不同意立项,批示“此事今后不要再议”。我们为此屡次晋京拟拜访S说明情况,但其始终不予接见。我们只得反复与德方协商,并再度赴德,最终使其将投资额降为2亿马克。但S仍坚持己见,毫不松口。
3年4月,卫生部崔月犁部长率团去日内瓦出席第36届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大会,我奉派作为顾问随行。会后,我陪同崔部长访德,并与医院公司再次会谈。联邦卫生部长亲自接待和主持会谈,最后德方又一次同意将投资额降为1亿马克,并提供低息贷款。对方反复强调,一再降价的目的是希望在中国市场占有一席之地,即便赔本也干,并拟联系相关的德国医院设备。
回国后,我们手持崔部长给S的亲笔信,再次拜访国家计委。S仅指派一位司局级干部对我们说:“崔部长把什么事都推给我们,国家已给卫生部拨款,请你们自己解决!”裘教授和我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搬动同济老校友、前任卫生部长钱信忠,一起拜访S。后者仍避而不见,仅指派两名司局级干部接待,告知S的意见是:“若对方以无偿方式赠送,我们就可接受。”是日北京下着倾盆大雨,当时的情景和失落的心情我至今未能忘。
至5年,裘教授和我再次专程赴京,承蒙原湖北省委书记、时任党中央书记处书记陈丕显在中南海官邸接见。经他联系,负责外经贸工作的谷牧副总理接见了我们。我们向其扼要汇报来意,说明德方愿以年利率5%的低息贷款资助我们完成此项计划。他允诺,若果真能获得这笔低息贷款,则由他负责与国家计委沟通。我们心里又燃起希望之火。
为此,我们于5年6月又一次赴德,与医院公司举行会谈,要求将贷款利率降至5%以下。对方答应努力争取,但为避免其他第三世界国家起而仿效,拟以免费提供整套设备等方式,使折算后的贷款利率低于5%。我们也完全同意这一做法。
回国后,我们从陈丕显书记处获悉谷副总理在京,但联系后其秘书却告知谷已去外地考察,无法会见。闻此言,我们明白谷副总理必定在S处碰了钉子,故不便接见。回校后,作为最后一搏,裘教授和我以个人名义给谷副总理写信,汇报了与德方商谈的结果,并强调我们已按其指示争取到低息贷款,希望他能继续支持该项目获得批准。两周后,接到谷副总理秘书的电话,告知已将此事通知卫生部和国家经委,让我们直接与这两个部门联系。显而易见,谷牧也未能改变S的决定。
6年,德国医院公司Dargatz经理医院事宜,卫生部通知裘教授和我赴京参与接待。会谈中,德方认为两国部长议定的项目应视为政府间协议,且德方已为此付出大量人力物力,故协议应予落实。卫生部领导则表示目前我国有困难,该项目须待我方经济情况好转后再予落实,并对此表示歉意。事后,Dargatz单独宴请裘教授和我,他说生意不成友谊在,期望今后有机会合作。
我们历经长达六年的千辛万苦,仅凭S一句“此事今后不要再议”的批示,最后功败垂成,令人心酸、悲愤和痛心!难以理解的是,为贯彻中央改革开放的方针,要想为国家做点事,为何如此困难!
后记
笔者从武老所撰《百年沧桑母校情——亲历同济医学院校史鳞爪》(即《自述》)中摘录相关章节(原文篇幅较大,已对文字进行删节),作为“追忆武忠弼教授”一文的补充。
《自述》如实地重现了改革开放之初的一段历史,使我等后来者得以获知,前辈们为学校发展所付出的心血、取得的成就及遭遇的挫折。如今被视为理所当然的一些事,前辈们当年须克服难以想象的重重困难,即使遭受怠慢、难堪和非议,甚至承担一定风险,仍然百折不挠、勇往直前。
必须强调的是,武汉医学院(同济医学院)当年的领导集体及其他老教授共同谱写了我院历史上的这一页。武忠弼教授则是其中的杰出代表之一。
当下,同济医学院的办学条件已远胜当年。不忘前辈们创业的艰辛,传承前辈们严于律己、忠于职守、热爱母校的品德,是对他们最好的纪念。
多余的话
评价生者或逝者均非易事,所谓见仁见智。武老并非完人,其工作中的失误在所难免。尤其是,文革结束之前的近30年间,各项政治运动从未间断,缘起高层领导对“治国方略”的政见分歧及权力之争。但政治运动一旦波及基层,其后果必然是群众斗群众,概莫能免。个人置身其中,在不同时期或场合,或沦为受害者,或有意、无意地伤及他人,由此遗留某些难以化解的恩怨。
笔者并非在同济完成大学学业,无意、更无资格评说同济过往历史事件的是非曲直。我所认识的武老,是痴情同济,为母校发展而呕心沥血、无怨无悔的长者。值此武老逝世10周年祭,特撰文缅怀这位令人敬仰的前辈。
同济医学院免疫学系教师龚非力
.11.06
赞赏
人赞赏
转载请注明:http://www.jichuc.com/dzys/850.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