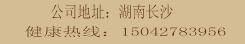艰辛农活种种
对于农民来说,革命与否并不重要,阶级斗争也于己无关,种好庄稼有饭吃才是头等大事,下地劳动几乎就是他们生存的全部内容和意义所在。
万村原来没有电,(后来买变压器通电用的还是知青的安家费,直到我离开万村,村里也没有给知青盖房子)没有农业机械,畜力又有限,劳动全靠人力。不仅要耕地,而且要爬山,不仅抡锄头,而且要挑担。我在万村经历了六个春秋,差不多干遍了所有的农活。
春耕是最繁忙的季节,要耕地、施肥、播种。耕地分人力、畜力两种。大一点的地块用畜力拉犁,我试过,但扶不好犁,耕出的地垅七扭八歪,深浅不一,牲口却累得不行。扶犁是个把式活儿,队里不会让我们干。小块的地则完全靠人力,几个人一字排开,抡起板锄,一锄一锄地把地翻一遍,十分原始,效率极低。我想,这便是“修地球”的由来吧。年以后,村里开始花钱雇拖拉机耕地,也只是解决大的地块,其余的仍然是靠抡锄头。
说起锄地,春耕不算苦,要命的是秋后深翻土地。某年,不知是从哪儿传来的“先进经验”,说深翻有益。深要深到一尺以下,队长拿根小棍跟在后面量深度,插不下去就要返工,干几天下来,真把人累死。其实,深翻土地也要因地制宜。许多地方一尺以下都是生土,翻上来怎么种庄稼?干了一年,后来这“经验”被废止了。
施肥都是农家肥,一种是牲口粪,一种是人粪。
堆牲口粪叫做“起圈”,就是把马、驴、骡、猪赶出圈,把它们日积月累、掺杂了泥土的粪便撬起,掘出,一担担挑到村口堆起来备用。牲口棚里的味道很冲,干一会儿就要出来透透气,不然真要窒息。猪圈是露天的,但圈里常常是稀稠的粪便,不似牲口棚里的干燥,踩下去很滑,若滑倒就麻烦了。而且,久积的粪便经过翻倒,气味十分难闻。万村没有养羊,但会请路过的外村羊群在自己的地里(一般多在山上)过夜,以留下羊粪肥沃土地,称之为“卧羊”。我曾到山上去给羊倌送饭。一副担子,挑着小米稠饭外加清炒北瓜,一路上很难保温。到得山上,一阵风刮来,稠饭就蒙上一层灰,我们撅下干树枝,撕去树皮,就做了筷子,吃得很香。毕竟,那稠饭是难得的“好饭”了。其实,羊倌是个苦差事,带着羊群,一卷铺盖一把伞,风餐露宿几个月不得回家。如果不是太贫苦,一般人家都不愿让孩子做羊倌。
使用人粪叫做“挑茅”,即把各家茅间的屎尿用一个特制的长杆小翻斗捞上来,装入桶里挑走。粪坑里上面的稀,下面的稠,而且味道也越来越浓。因为从各家挑茅是按桶记帐,要算工分的,所以各家常常会在挑茅前灌水,套用今天的话,这叫“注水粪”。一般情况下,不会把茅坑挑干,因此也不必下茅坑。若是遇上“起茅”,工程量就大了。要先淘干上面的稀稠部分,再把茅间的条石挪开,人下到茅坑里去起底。那都至少是几年的积淀了,已经变成了黑泥,并伴有浓烈的氯气,不晾一晾,通通风,人都不敢下去。在茅坑里挑粪、装桶,上面的人拉上去,一不小心就会淋你一身,满头满脸。人粪挑出来要与泥土混合搅拌,放置几天,否则太过浓烈,会烧死庄稼。
挑牲口粪比较干躁,用簸篮即可,一挑四五十斤。挑人粪要用木桶,咣咣当当,一担要七八十斤。我们每天挑十几趟是很平常的事。有一次,老乡之间打赌,一个后生一次挑了六桶大粪,足有二百多斤,而且要一口气挑到山上。他赢的赌注,不过是一盒一角三分钱的烟卷。
无论起圈、挑茅或担粪,都是和屎尿打交道。起初我们还小心翼翼,生怕溅到身上,其实根本不可能避免,结果总是浑身恶臭。每次收工,我们就把衣服脱在院里光身进屋,出工时再穿。挑粪的活干完了,一身衣服也沤烂了,索性扔掉。
播种就显得轻松多了。种谷子、小麦用牲口拉摇篓,没有牲口就用人拉,一陇陇播过去。种玉米、高梁则靠人工,前面一个人在耕松的土地上刨坑,一锄一个交错前行,深浅、间距很有讲究,算技术活儿,都要老农把式。中间一个施肥,提着粪桶,用类似钢盔但有把手的陶制器皿舀了稀粪,一个坑一个坑地浇过去。后面一人撒籽,每个坑里丢下三五粒,然后用脚掩埋。这样三人一组,依次排开,十分有序。一般情况下,知青只管挑粪到地头,那施肥、撒籽都是女人、孩子干的活儿,知青女生中有体弱的,也加入他们的行列。
播种之后是间苗。几场春雨过后,地里一片葱绿,小苗长势很旺。撒下的种子长出来都是一丛丛的,需要锄掉弱的,保留壮的,并形成一定的间距。玉米、高梁间苗用勾锄,看准了,一锄下去解决问题。我们初学,常常一锄毫发无损,再锄却又“全歼”,弄得老乡哭笑不得。间谷苗就要用手了,蹲在地上,一棵棵去挑选,缓缓移动,干一天下来,真的腰酸背痛。插队第一年,我就是因此一度患了双脚神经麻痹,走路都不稳,差点瘫痪。
玉米长到一人高以后“挂二锄”,即松土、保墒,这是农活中最难受的。时令已是入夏,庄稼长势正旺,超过人头,地里密不透风,人钻进去立时一身汗水。光着膀子会被叶片刮得伤痕累累,汗水一浸尤其痛苦。若穿衣服,则大汗淋漓,时间长了,若不出来透透气,非中暑不可。“挂二锄”是我最怵头的农活之一。
夏收割麦子,出工收工两头不见太阳,中间晒死人,吃饭都在地头,真是“龙口夺食”,凡干过的没一个不叫苦。我本就体力弱,又是左撇子,用左手镰割得更慢,总是落在后面,不仅自己难堪,而且影响进度,后来队里索性不让我割麦了,派到麦场去帮忙。扬场讲究风向、力度,更是把式活儿,我只能做赶驴压碌碡、扫麦秸的辅助小工。过去,我们不懂为什么要“抢收”,干了几年农活,特别是在夏天大雨中抢麦子、苫麦垛,才知道,麦子遇雨会倒伏,麦垛会发芽,倒伏和长芽的麦子就毁了。我们插队的第一年,万村麦子亩产才96斤,到我离开时,也不过斤。夺下的这点食,真是可怜。秋收就好多了。男人们把高梁、玉米割倒,女人、孩子掰(割)下果实,再一车车、一担担运回村。收获总是喜悦的,苦点累点大家也认了。
在农村,挑担子几乎是每天必不可少的劳动。生活中挑水就不说了,劳动中挑土、挑粪、挑粮食、挑各种散碎东西都离不开担子,而且要爬坡、涉水,还要学会换肩。最初参加劳动,正赶上春耕末尾,我们每天要挑粪到地头,开始还用垫肩,但几天下来,不仅腰酸背痛,而且肩膀红肿,甚至破皮。到我离开万村时,挑担子已是稀松平常事儿,如果不是很重,简直可以说优哉游哉了,光着膀子也照样辗转腾挪。多年以后,工作中参加义务劳动,我挑担子的功夫,还常常令同事赞叹。某年,在海南莺歌海盐场采访,为了体验挑盐女工的辛苦,我们几个记者轮番上阵。一担盐百十斤,多数人挑不动甚至根本挑不起来,我却应对自如。
万村有林业、果木业,我干过种植苗圃、给果树喷农药、嫁接、修剪树苗等活儿,比庄稼地里轻松许多。
万村的果树以桃、梨、苹果为主,但品种很差,且逐年退化,产量不高,除了自己吃,似乎没听说卖过什么钱。即使卖,每斤也不过一两角钱。我在林业队劳动,近水楼台,从春天的杏、李、桃,到秋天的苹果、梨,吃了不少。虽然品种差些,也算弥补了缺乏青菜和维生素的不足。不过,敢偷果子吃的也就是知青,老乡若偷,是要罚工分的。至此,当初向我们宣传的“农村美景”顺口溜的最后两句“走路不小心,苹果碰了头”,也被证明是假的。
村里的副业有油坊、粉坊和砖窑。榨油、磨粉都是技术活儿,知青干不了。我只会推石头碾子,给自己加工一点粮食。其实,一边推碾子一边翻扫粮食,也需要“技术”,知青做,常常要请村里的大娘、大婶帮忙。砖窑上最苦最累的活儿是和泥、脱坯,其次是背坯、装窑,前者需要耐力,后者要下死力,干一天回来,人累得如同散了架,连饭都不想吃。相对而言,烧窑后担水窨窑、灭火晾窑就轻松多了。但出窑则不光要卖力气,还要注意安全。那时,窑里还是热的,即使只穿一条短裤也恨不得快点出来,取砖不免就近,有一次我就因为图快,抽松了砖垛,结果塌下一片,埋住半身,险些把我砸死。
此外,用我们的建房款通电之后,村里在最大的那块四十亩修了一条渠,准备把河水抽上来浇地。为了修渠,我们没少挖土方,修成之后却没怎么用,后来竟荒芜成了一条土埂。我们做了无用之功。
工分里的“政治”
参加劳动就可以记工分,工分就意味着收入,但计算起来,却不是个简单的经济问题,而且比较复杂。
我们每天的劳动时间分三段:天蒙蒙亮就下地,太阳出来了收工,回来吃早饭。饭后再下地,干到中午。午饭后可以休息,下午两点左右再出工,直到天黑。一年中,除去冬闲,这规律几乎不变,即使下小雨也照样出工。雨下大了再回来。
上工靠敲钟,收工听吆喝。早晨、上午、下午三段,只要全勤,就会分别记上两晌、四晌、四晌。“晌”是劳动时间的计量单位,但不等于工分,更不代表分值。工分是要评的,办法是“自报公议”,要开社员大会。评工分的办法来自当时的农业红旗——大寨。评工分并不以劳动时间、数量和质量为全部依据,还要评思想、评劳动态度。按照正常情况,一个男劳力一天干10晌应该是10分,(极个别的可达12分)女劳力或半劳力(孩子、老人)在6分到8分。就是说,即使全勤,也只相当于男劳力工分的60-80%。我们下乡之初,往往因为“劳动态度差”,或者“思想有问题”(譬如不听队干部的话,或关系不好)而被降低等次,本应评为10分的,成了9分、8分。插队后期,才基本正常了。
有了工分仍不能换算成货币,要等全年收成最后算下账来才能确定分值(压低某些人的工分,也是为了减少工分总数,尽可能提高本来就很微薄的分值)。例如,以某年全村总收入若干做分母,以全部劳力的工分总数做分子,平均下来,如果折合每个工分5分钱,就是说,一个男劳力干一天,以10分计,可以挣5角钱。假如全年出工天,且全部为10分,则合元,一家人扣除了口粮款、公积金以及日常分些油、肉、菜之类,也就所剩无几了。辛辛苦苦干一年,反而倒欠村里的事所在多有,譬如知青。假如我一年出工天(这在知青中算是多的),每天工分8分,每分5分钱,一天就是4角钱,全年折合80元钱,而一年的口粮款至少需要50元,再扣除其他,还能剩余多少?以年为例,万村全体知青19人(原来20人中有1人转走了)就有14人欠账,占全村欠账总额的15%;我个人欠账27元。年春节,大队给在天津的我们寄来这份结算表,声明:不交欠款不给粮食。同学们说,这不仅是要账,而且是威胁。因此,有的同学只能自己掏钱买口粮。还曾听到一个笑话:某社员干了一年,年终算账,分红拿到2分钱,气得他拿了这枚硬币就扔到茅坑里去了,结果连个响儿都没听见。
劳动不以质量计算,工分的“政治化”,严重挫伤了农民的积极性。“上工如拉纤,收工如射箭”,就是劳动“大锅饭”后果的形象比喻,也反映了人们对劳动报酬不合理的消极对抗。如此,还谈什么劳动效益?
年,为了提高粮食产量,上级号召大量种植高粱。那种高粱是矮杆型,产量确实高于其他品种,但壳子也很硬,很难脱下来,当地称为“戴帽茭子”。这种东西不能交公粮,只能喂牲口,但可以算产量。村里分给我们的口粮里就有这种高粱。因为脱不净壳,大家就凑合吃,结果连解大便都困难。恰好县里派知青慰问团来了解情况,我们就告了状。没想到,村干部挨了批评,回来就报复,每个知青的工分都被降了等次。
并不是所有的工分都需要付出体力劳动,譬如为集体提供农家肥,就可以记工分。此外,开会、出差也可以记工分,当然,那是村干部们的“专利”。他们还有其他补助工分。
我在村里五年半,除去“修地球”,还有两个途径可以挣到工分。
一是写黑板报、刷标语,算是宣传工作,脑体结合。写一天可以挣8分,毕竟比到田里干活轻松。只是村里的黑板报其实没几个人看,完全是政治需要,装装门面。这样的活儿也有限,一年写不了几次,也占不了多少便宜。奇怪的是,离开20多年以后,我几次回村时都发现,我用过的黑板、刷过的标语,居然还有残存的痕迹。都说世事沧桑,万村怎么就不变呢?
二是看青、护秋,即保护从灌浆后到收割前的粮食不被人偷。在庄稼地里转一天(包括夜间),可以记10分。村里如此安排,自有一番“道理”:知青偷粮食,不过是充饥、解馋,一人吃饱而已;农民偷粮食却是实打实过日子,防不胜防。再者,知青在村里无亲无故,捉人可以不讲情面,严格“执法”。因此,从年起,我连续三年都肩负如此“重任”。当然,也因为“铁面无私”没少与老乡吵架,甚至动手,但也挣下一些工分。
我插队近六年,除了领齐口粮,分些副食外,一分钱现金都没有挣到过,临走还欠大队20多元。即使干得最多、工分最高的年份,也只落得不欠钱而已。而大多数同学甚至不如我。当然,这里面不排除知青劳动时间短、工分少的因素。但分值太低是决定性的——我在万村期间,没有一年结算的分值超过7分钱,即每个全劳力每天最多挣不到七角,即使一个当地壮劳力的农民,一年苦挣苦熬,也只能落得养家糊口,很难挣下富裕钱。
“科学实验”与菜园
年,不知是哪一级下达了任务,要求各村搞育种科学实验,代号“五四0六”(我始终没有弄清楚那是什么意思),据说有助于优化种苗质量,提高粮食产量。这任务就交给了知青。我们一天化学课也没学过,根本不懂那些分子式和专业术语,那几个同学每天关在粉坊里,照着书本培养菌种。搞来搞去,没有任何成果,只好收摊。
山西的野生酸枣树很多,万村北山上到处都是。那年,又推广了不知是哪里的经验,搞“酸枣接大枣”试验。据说,搞好了就可以把满山遍野的野生酸枣树都嫁接成人工培育的大枣树。我参加了这个试验,整天跟着老农满山去搞嫁接。方法就是在酸枣树枝上割一个“T”形的口子,把从大枣树上切下来的嫩芽塞进去,捆扎好,隔几天去看看,长在一起了,就算嫁接成活。据我所知,成活的不少,但却并不见酸枣变大枣,这项“科学试验”又失败了。
说到科学,顺带说说当年万村的医疗卫生条件。医院,公社有卫生所,村里却只有一位人畜兼治的“赤脚医生”。老乡们有个头疼脑热,大多靠土法子自己诊治。如果是受了风寒,就用纳鞋底的大针,在额头上扎几下,挤出黑紫色的血来;如果觉得是“上火”了,就端一碗凉水,取一块烧红的煤炭放进去,“呲啦”一声之后,趁热把那还漂浮着煤渣的水喝下去。我至今不明白那其中有什么道理,但老乡们用这些办法确实治好了病。也有类似游方郎中的医生来村里巡诊,但治不了大病。如果有了急症,则大多要看个人造化了。我的房东老鲍,在地里干活时突发肠梗阻,如果不是附近驻军的医生赶来,在地头为他手术,他就没命了。另一位王老汉夜间发病,找不到医生,他老伴来找知青,问我们有没有办法。有位同学自告奋勇,说会做心脏按摩,去了以后,骑在老汉身上就按,劲头倒是不小,但毫无效果,天未亮老汉就一命呜呼了。后来说起此事,我们都说,没准儿就是那几下“按摩”要了老汉的命。(说来也怪,那位“按摩”的同学,后来竟也因心肌梗死英年早逝了)不过,即使是送到最近的公社卫生所,恐怕也无济于事。医院,20里的山路就是一大障碍,况且,县医院的条件也很差。我为了治病曾多次去过,那里的诊室、病房又脏又乱,比起大车店也好不到哪里去。依我看,住在那里,没病的也得有病,有病的会更严重。
年,为了解决老百姓的吃菜问题,村里终于决定在村边开出一块地种菜了。我因为身患肝炎的缘故,被“照顾”到菜园干活。
那菜园大约有三、四分地,种了卷心菜、小葱、菠菜、大白菜之类,我还曾引进过西红柿、西瓜试种。菜园由两位老农负责,一个叫王群则,一个叫张妈孩。群则是抗战时期的老党员,牺盟会敢死队员,按说也是“老革命”了。不过,后来部队南下,他因为恋家开了小差,半路跑回了村里,从此就成了地道的农民。妈孩一辈子务农,没听说干过别的。两个人都五、六十岁了,我算壮劳力,于是,挑粪、浇水是我的活儿,他们只管伺弄蔬菜。
挑粪的活儿我已习惯。进村时发给我们的扁担,已经成了我不离身的工具,而且磨得油光水滑。浇水却是新的苦活儿累活儿。种菜需要大量的水,每天都要浇灌。菜园旁边有一口井,深约十几米,井台下挖了一条露天的土水沟,通向菜园,菜园里的菜畦以沟相连,我的任务是从井里打上水来,倒进沟里流向菜园。群则、妈孩负责一畦畦放水、堵口。那水要用一个柳条编的大斗,靠辘轱摇上来,一斗至少五六十斤重,不停地放下去、舀满水、摇上来、倒掉、再放下去……周而复始,不仅机械、单调,而且非常吃力。每天开始浇灌时,最初的水总要先把土沟浸透才能流淌,待流进菜园,没有几斗水是浸不透的。就这样不停地打水、倒掉,再打水,再倒掉,中间不敢停,一停水流就断,群则就会喊叫起来。如此一天下来,腰酸背痛。我曾要求队里派头驴来拉水车,省去人工。但畜力有限,驴不常来而我常在,我只好代替驴来干。后来,队里看我一个人实在无法满足不间断地供水,就又派了一位男生来,柳斗也改成了水桶,份量轻了,再加上两人轮替,好了许多。
菜园的两个老农虽然朴实,却也挺“狡猾”,知道我们年轻,干活不惜力,又不大在意工分,因此总是把脏活、累活分配给我们,他俩只管在园子里转,干些轻活。看着他们悠闲地坐在田埂上抽烟、聊天,我们很生气,就想方设法以偷懒对付。
办法之一,就是故意把水桶扔到井里,然后喊群则他们来捞桶或者自己干。在十几米深的井里捞桶很麻烦,要用绳子拴一个铁锚放下去,在水里慢慢地盲目寻找,感觉铁锚碰到水底的桶了,轻轻侧拉,锚钩才能把桶挂上,再慢慢提出水面。若挂得不牢靠,常常半途而废,一切重来。捞一次桶,怎么也要个把小时,我们乐得趁机休息。
偷懒的另一个办法是谎报时间。我有手表,看看时间差不多了,提前就喊:“王大爷,到点了,该收工了。”群则他俩疑惑地看看太阳,宣布收工,我们便一溜烟地跑了。几次下来,王老汉发觉不对,说我的表不准,根据是——“我回家半天了,喇叭都没响!”原来,村里有有线广播,给许多人家装了一个小喇叭匣子,公社广播站定点开播,成了时间的参照。我辩解说,怎么会是我的表不准?肯定是公社的广播员忘了时间。群则将信将疑,后来还是决定以看太阳为准,不信我的表了。那水桶也被拴死在绳子上,再也掉不到井里了。我们偷懒的招数均告失效。
那年,菜园里小葱种多了,村里吃不了,队里派我出去卖掉,换点收入,并且说价格可以由我做主。我挑了一担小葱到周围几个村子去叫卖。其实,不用吆喝,凭我的“大学生”身份,把担子一摆,问一声周围的人要不要,老乡们就像看稀有动物一样围了过来,妇女、孩子的指指点点和悄声议论,还让我挺不好意思。有老乡说,没有钱,用鸡蛋换行不行?我想,鸡蛋可以自己吃,我把钱交给队里也一样。于是同意换。半天下来,一担葱居然卖光了。
回村的路上,我坐下来数了数给自己换的鸡蛋,正算着应该交给队里多少钱,远远地有一群人说说笑笑走了过来。定睛一看,竟是东峪村的知青,彼此都熟悉,让他们看到我这幅模样,怎么好意思?我赶紧拉下草帽挡脸。那边却已经有人在叫我的名字:“张刃,干嘛呢?”我无奈地站起来:“这不卖菜呢嘛。”“你行啊,会做生意啦。“呦,还会换鸡蛋呐。”男生女生嘻嘻哈哈拿我打趣。我故作潇洒地说:“咱这也是锻炼,还落得清闲。”他们去赶集,一个个穿着光鲜,我却破衣烂衫,头戴草帽,挑副担子,显得越发寒酸。望着他们的背影,我心里挺不是滋味。回村后,我把钱如数交给了队里。
为了调剂蔬菜品种,我让家里寄来了西红柿和西瓜种籽,还有相关的书籍,照猫画虎,试种了一季。不知是什么原因,长势不好。西瓜只结了两个,还没有菜瓜大,被我们几个人囫囵吃了。西红柿倒是结了果,稍微红一点的都被我们悄悄地吃了。群则、妈孩天天守着,就是不见成熟的果实,起初纳闷,后来明白了,也不再管。第二年,说什么也不种了。
生活改变了轨迹
年底,全县知青大规模招工,万村知青走了三分之二。分配了工作的同学去报到了,没有分配的回了天津,村子里只剩下我一个知青。我变得心浮气躁,生活也完全改变了正常轨迹,并且第一次动手打了村里的老乡。
那天,我被队里派到山上去砍圪针(酸枣刺),运回来扎篱笆用。那活儿很不好干,要时时提防被扎破手,可又必须用手去抓。砍了一上午,收获不大,我把砍下的圪针聚拢成两捆,用尖担挑下山来。
尖担是一种特殊的扁担,两头包了铁尖,专门用于挑麦捆之类。谷子、麦子、青饲料扎成捆,先用尖担的一头插牢,挑起,再去插第二捆,然后挑起担走。这中间的那一步最难,等于扛着第一捆去挑第二捆,搞不好就会失去平衡。挑圪针是同样的程序,虽然重量较轻,但很容易被扎破什么地方。那天,我的手破了,衣服也被刮了口子。
我挑着圪针进村,碰上二队会计黑孩,他说:“张刃不简单啊,一上午就砍了这么一几几,(长子话“很少”“很小”的意思)够烧一锅水了。”分明是在挖苦我不能干活儿。周围的老乡跟着起哄,我恼羞成怒地摔下担子就冲了过去,问他什么意思?他说:“你干这点活儿就想混工分,不能记。”我说我不稀罕那几个工分。他说:“你们这杆人,就是能吃不能干。”接下来就是恶语相向,对骂起来。长子人对骂都是恶狠狠的,但极少动手。而我最不能容忍的就是对方污辱自己的人格。我见他越骂越难听,而且骂起了所有的知青,一时火起,突然出拳直捣他的脸面。只一拳,他的眼睛就肿起来了。老乡们决没有想到我会动手,一时间竟楞住了,紧接着就吵闹起来,说,这还得了,敢打咱万村人!他们极力怂恿黑孩还手,自己却袖手旁观。
这是我到万村后第一次动手打人。当时真的不顾一切了,顺手抄起了尖担端在手里,大声喊:“有胆儿大的就上,看我敢不敢捅死你!”事情闹大了,村干部和同学们都跑来劝架,总算没有发生更大的冲突。只是黑孩的眼睛过了好几天才消肿。事后想想,真不该动手打人,是我因为选调不顺利,心浮气躁,犯浑了。(44年后的年春天,我又一次回万村,在村口,就遇到了黑孩,他已经年过古稀,说起当年打架的事儿,彼此哈哈一笑,俨然多年老友)
年以后,万村只剩下七个在册的知青了,而且大多常住天津。多数日子,村里只有三两个同学,甚至只我一人。村干部知道我们迟早要走,既不要求我们参加劳动,更不管我们做什么。我虽然属于在村里的坚守者,但坦率地说,参加劳动很随意,谈不上吃苦受累了。不过,从年起,我在村里连续三年担负起护秋的任务,这个活儿每年要连续干三个多月,连带秋收,也能挣点工分,而且我自认为是认真的,但不敢说负责——因为我们也“偷”。
护秋的活儿,是村干部主动提出让我和另一个同学小璐干的。他们觉得,反正我们迟早要走,不会踏实劳动了,而且免不了“偷”些吃食,莫如让我们干点村里人干不了也干不好的事。护秋需要铁面无私,不怕得罪人,让知青干最合适。
其实,护秋的工作很简单,就是每天不定时间、地点地到那几百亩庄稼地里去转悠,发现偷粮食的要制止,必要时可以扭送大队处理,更多的时候,是起一种“震慑”作用。因此,护秋成为我在村里干过的最“风光”的活儿——不用下地卖死力气,提一根枣木短棍,配一支手电筒,加上自制防身用的匕首,整天昼伏夜出,神出鬼没,俨然“管人”模样。
配备那些家什是必要的。短棍可以防身,手电筒用来照明,匕首则因为可能会有意想不到的遭遇。
一天夜里,我独自在玉茭地里巡视,忽然听到有“悉悉索索”的响动,远远看去,像是我们喂养的那条小狗。我没有在意,继续前行。但它并没有像往常那样很快来到我的身边,似乎总与我保持着某种距离。我有些警惕了,怕在庄稼地里吃亏,便迅速回到了小路上。它出现了。借着月光,我才发现它比我们的狗大了许多,特别是那尾巴,直直地竖立着。是狼!我不禁毛骨悚然,做好了搏斗的准备。也许那狼觉得势单力薄,不能放倒我;也许是我的手电筒发挥了作用,它停在了距离我几米远处。我们对峙着,几分钟的时间,我却感觉过了许久。那狼终于没有扑咬上来,而是转身迅速地消失在夜幕里了。从那以后,我每次出去都带上了匕首。
我怕狼,但不怕人。无论白天黑夜,发现有人在地里偷偷摸摸,都会毫不犹豫地跟上去。说来也怪,老乡还真怕我们。某夜,我和小璐抓到了一个偷玉茭的邻村人,在带回村里的路上,双方发生冲突,动了手,那人被我们打得够呛,看热闹的万村老乡也见识了厉害,村干部还表扬了我们,从此“声威大振”,连周围几个村都知道了万村有知青护秋,来偷粮食的果然少了。
那年月,老百姓小偷小摸弄点粮食,不过是为了补贴生活,真让他大偷大盗,一般人没那个胆量。所以,我们护秋,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一般情况下,很少与老乡较真儿。
也有不买账的。一天下午,我在玉茭地里发现同村的秋来老汉带着孙子在偷豆角,就劝他们赶快离开。老汉不理,反而嘟嘟囔囔骂我,而且很难听。我好心未得好报,不免起火,开始口头警告,没想到他骂得更凶,我一气之下动手了,只一掌就把老汉打蒙了,坐在地上起不来。我忽然意识到,打老头儿,惹祸了!于是撒腿就跑。转了半天才回村,没想到那老汉竟堵在村口,要找我拼命。我只好躲避到村外去了,天黑才回来。后来听说他去找支书“评理”,金玉领教过我的拳脚,反说老汉:“你偷豆角撞在他手里,还骂他,他打了你,我没法管。”结果不了了之。只是秋来老婆追着我骂了好几天,我自知理亏,只好忍气吞声。
其实,我们护秋也“偷”,但不过是弄点吃的果腹或尝鲜。村干部心知肚明,甚至暗示:你们要吃甚,只管吃,但别糟害太多。最好是去邻村地里。某夜,我们去山上刨红薯,挖得狠了点,怕不好交代,就有意从邻村方向绕了一圈才回村。第二天,支书金玉认真查看了脚印,果然认定被邻村人偷了,让我们多加注意。我们却暗自好笑。
既负责“保护集体财产”,又私下“监守自盗”,这便是我们的护秋生涯。说到底,这一切都与肚皮相关。
插队初期,大多数知青还是守本分的,也很诚实。半公开地“偷”些吃食,是下乡两年以后的事,开始也只是为了填饱肚子,增加营养。插队后期,吃饱已经不是问题。一则干活少了,也没那么累了,二则住村时间少了,政策规定的粮食定量反而有了富裕,有的知青还会倒卖“高价粮”以换取一些零花钱。(当时的玉米价格,国家收购每斤九分四厘,而黑市可以卖到四角五分,豆子更达到六七角)特别是随着陆续选调,村里剩下的几个知青与老乡们已经混得很熟,而且有了关系不错的朋友,别人也不大敢欺负我们,更知道我们迟早要走,吃点什么没啥大不了的。所以大多不再计较。队里也懒得管。
没有了果腹之忧,才有了为宣泄的恶作剧,荒唐事。以下所述各节,属于自爆丑恶,谨为忠实记录。
夏日庄稼正旺,与玉米间种的豆角也熟了,我们常去摘来做菜吃。这事做得半明半暗,队里也是睁眼闭眼。一般情况下,我们摘了豆角就塞进背心里,若有外套则略作遮掩;如果没有,鼓鼓囊囊的挺明显,也敢大摇大摆地进村。有时掰几个嫩玉米回来煮了吃,办法是把玉米一穗一穗插在皮带上,插一个松一下扣眼,转圈插满,活像子弹袋。外面罩上制服,一般也看不出来。一次,我和一男生腰间插满了玉米进村,远远地看到大队办公室门口围了一群人,走近一看,电线杆挂着两穗玉米,贴着一张纸条,上写“XXX偷的玉米”,显然是为了羞辱其人,杀鸡给猴看。我们腰揣“赃物”,还煞有介事地问村干部:这是咋回事?
年秋,有四个男生半夜跑到五里外的义合村去偷苹果,一下子竟搞了上百斤。结果地里留下了大量的胶鞋印和狗爪痕,义合老乡据此判断,是万村知青所为,天一亮就追进了村,人脏俱获。30年后我回长子,偶遇一位义合的中年人,居然还记得此事。我笑称,当年“案犯”下落我都清楚,可以一一指认。那人也笑说:“告诉他们,现在苹果有的是,尽管来吃,不必偷了。”我们大笑不止。
插队几年,我们吃的水果无数,虽然品质较差,但按照今天的标准,绝对属于“绿色食品”——因为万村根本买不起化肥。就品种说,吃的最多的是苹果。插队后期,我们偷吃苹果已经不再避讳老乡,宿舍里浓郁的果香也根本无法遮掩了。但老乡能够从品种判断出是否万村的果子,并且常常一起分享。
偷粮、偷菜、偷水果,无非为了填饱肚子,补充营养。但知青中有些人做的有些事,已经与吃无关,纯属荒唐。有的是恶作剧,有的纯属祸害人。
秋天,红薯将收未收时,我们半夜去挖,为的是尝鲜。红薯长在土里,有大有小,黑夜里很难判断,又不能明目张胆地干,只能挖一兜摸摸看,大的留下,小的丢弃。结果把一片地挖得乱七八糟,糟蹋了不少粮食。现在想想,真是造孽。
最无厘头的是,某次,我们在偏远的庄稼地里发现一个陈年墓葬,坟茔已经塌陷,露出了棺材。小璐那时正对做木匠活感兴趣,竟忽发奇想,说那棺材板是好木料,要“拿”回去。本以为他说说而已。不料,他半夜果然行动了,还叫我为他望风。我说,你可要弄清楚,那木头是浸渗过死尸血水的。他说,只要棺材盖,没问题。近百斤的长木板子啊,他一个人居然背回了村里他那间小屋!
(没完,待续)
本文作者张刃
预览时标签不可点收录于话题#个上一篇下一篇转载请注明:http://www.jichuc.com/dzyy/6357.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