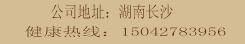![]() 当前位置: 肠梗阻怎么引起的 > 大肠梗阻萎缩 > 妇科手术后盆腹腔粘连预防及诊断的专家共识
当前位置: 肠梗阻怎么引起的 > 大肠梗阻萎缩 > 妇科手术后盆腹腔粘连预防及诊断的专家共识

![]() 当前位置: 肠梗阻怎么引起的 > 大肠梗阻萎缩 > 妇科手术后盆腹腔粘连预防及诊断的专家共识
当前位置: 肠梗阻怎么引起的 > 大肠梗阻萎缩 > 妇科手术后盆腹腔粘连预防及诊断的专家共识
制定者:
医院学会
(CRHA,ChineseResearchHospitalAssociation)
妇产科专业委员会
出处:
中国微创外科杂志..20(6):-.
妇科手术后盆腹腔粘连是指手术组织/部位损伤后,在组织愈合过程中发生的一系列病理生理过程和结局,粘连所致的疾病包括女性不孕/不育肠粘连/梗阻、慢性腹痛/盆腔痛等多种并发症,并增加盆腹腔再次手术的操作难度。医院学会妇产科专业委员会组织有关专家制定本共识,通过分析妇科手术后盆腹腔粘连发生的流行病学特点、粘连形成机制和相关的临床结局,总结盆腹腔粘连风险的评估系统。本共识遵循循证医学理念,对有关治疗或干预方案给出循证评价[1])(表1),以期综合评估有关降低妇科手术术后粘连形成的各种方法的有效性,进一步规范我国妇科手术后盆腹腔粘连预防的临床规范。
01术后粘连的流行病学特点及发生机制术后粘连是困扰妇科医生的术后并发症[2],60%-90%的妇科患者盆腹腔手术后发生不同程度的粘连[3]。苏格兰手术与临床粘连研究学组(SurgicalandClinicalAdhesionsResearch,SCAR)综合分析妇科手术患者的手术记录和术后并发症[4,5],观察到约1/3经历开放性腹部或盆腔手术的患者,术后10天内发生2次或2次以上明确的或可能与粘连相关的并发症。李晓燕等[6]的回顾性临床资料表明,有腹部手术史再次因妇科疾病指征行腹腔镜手术患者,腹壁切口下粘连发生率为40.6%,其中切口下大网膜粘连占59.4%,肠管粘连占40.6%。Ellis等[4]对例开腹手术进行10年的随访研究,有35%的患者在术后10年内因粘连再次入院治疗,其中22%的患者在初次手术后1年内发生粘连,随着手术后随访时间的延长,粘连相关的并发症仍会持续存在。大部分患者主诉为轻度腹部不适症状,部分患者可能会继发肠梗阻、不孕、慢性盆腔痛[7,8],盆腹腔粘连导致再次手术难度增加、手术时间延长、副损伤增加等诸多临床问题,因此,妇科手术医生应在术前尽量评估粘连发生的风险,并在术中采取适当的防粘连措施,以降低粘连并发症的发生。
粘连是组织损伤后修复的结果,与手术所造成的锐性、机械性或热损伤、感染、热辐射、局部缺血、脱水及异物反应等多种因素有关,在组织创伤基础上继发一系列反应。首先,手术损伤部位的基质肥大细胞,释放大量组胺、激肽等血管活性物质,局部血管通透性增加,局部组织在缺氧基础上发生氧化应激损伤,局部大量游离的氧、氮自由基进一步诱发局部炎症反应,加重组织损伤。随后,纤维蛋白在局部沉积,内含大量渗出的白细胞、巨噬细胞,此后通过纤维蛋白沉积和间皮细胞增殖完成组织的愈合过程[9]。与皮肤切口愈合不同,腹膜损伤的修复起始于底层间质。因此,无论创面大小,腹膜的愈合速度相对更快,手术创伤后3小时内创伤部位即有纤维蛋白渗出。正常情况下,腹膜纤维蛋白沉积为一过性病理生理过程,72小时内即由纤溶系统清除降解。在局部损伤时,纤维蛋白沉积与纤溶系统的动态平衡被打破,纤维蛋白沉积占据优势,形成早期粘连。随后,纤维母细胞与血管侵入,局部血管化,形成永久性粘连[10](见图一)。总之,术后腹腔粘连起源于腹膜损伤,启动于炎症反应,爆发于局部修复,其病理生理过程迅速、级联且具有一定的复杂性。
02粘连分级标准及相关不良临床结局2.1粘连分级
目前,临床上多参考年美国生殖医学学会(AmericanSocietyforReproductiveMedicine,ASRM)粘连改良的分级标准[11](见表2)。
2.2盆腹腔粘连相关不良临床结局2.2.1不孕症
手术后粘连可影响双侧附件的解剖结构,干扰配子、胚胎的运输,进而影响患者生育能力。23%腹部手术史的患者因不孕症接受相关治疗[12]。目前唯一针对粘连松解与不孕症的相关研究为一项小规模的回顾性分析,研究对象为例腹腔镜探查术中诊断附件粘连的不孕症患者,观察组69例接受粘连松解术,术后12和24个月的自然妊娠率分别为32%、45%,对照组78例明确诊断后未进行粘连松解,术后12和24个月的自然妊娠率分别为11%、16%[13],依据ASRM粘连分级标准评分,足月妊娠率与手术时粘连评分呈负相关关系[14]。粘连形成影响患者的生育结局,导致不孕症的发生,与不孕症存在明确的相关性(证据等级B2)。
2.2.2粘连性肠梗阻
粘连性肠梗阻是小肠梗阻最常见的致病原因[15],肠梗阻患者中腹腔粘连所导致的肠梗阻占比约为74%[16]。20%以上的手术患者在术后第1年即出现粘连相关临床症状,其中因小肠粘连性梗阻再入院率约为4.5%[5]。资料表明,妇产科手术相关粘连性肠梗阻的发生率为1.2%-3%[17,18]。在妇科手术中,子宫切除术后更容易继发粘连性小肠梗阻(证据等级A1)。据统计,因良性疾病行子宫切除术,术后粘连性肠梗阻发生率为5.9%[19];从手术路径分析,腹腔镜子宫全切除术后粘连性肠梗阻的发生率低于经腹子宫切除[20]。
2.2.3慢性腹痛/盆腔痛
据不完全统计,妇科或胃肠道手术后慢性腹痛/盆腔痛的发生率为20-40%[7]。目前关于慢性盆腔痛与术后粘连的关系尚不明确。粘连的严重程度与疼痛程度之间也无直接因果关系。研究显示,粘连松解术仅对存有致密性肠粘连的患者有缓解疼痛作用[7,21];粘连松解术后再发粘连的几率和程度依然无确凿证据可循。目前所采取的预防和降低粘连形成的措施,尚无确凿证据证明能够有效降低术后慢性腹痛/盆腔痛发生率。肠粘连松解术或附件粘连松解术对缓解慢性腹痛/盆腔痛的价值尚难准确评估(证据等级C2)。
2.2.4增加再次手术的难度
粘连会显著增加再次手术的难度,包括二次手术时肠道损伤等并发症的发生率,术中操作技术难度加大,手术时间延长,导致术后愈合和恢复时间延迟,并增加术中输血的几率。tenBroek等[23]针对盆腹腔手术后粘连的meta分析,包括39项研究例患者,结果表明,再次腹部手术时,因粘连导致肠切除的总体发生率为3.3%(95%CI:2.5%-4%,I2=86%);其中16项研究涉及例患者,再次手术时一并行粘连松解术,肠切除发生率为5.8%(95%CI:3.7%-7.9%,I2=89%);再次手术时间较初次手术平均延长15.2min。手术的器官/部位也是粘连发生的重要因素之一,在开放性妇科手术中,涉及卵巢的手术最有可能并发术后严重粘连。手术路径也是粘连发生的重要因素之一(证据等级B1)。SCAR一项对例盆腹腔手术史患者的临床资料分析[24]显示,腹腔镜手术较开腹手术可以降低粘连相关再入院风险32%。
03妇科手术盆腹腔粘连防治策略3.1术前及术中粘连风险的评估
由于大部分术后粘连缺乏症状,目前尚无有效的无创检测手段判断粘连的程度及预判粘连可能造成的不良影响。目前上市的个别防粘连产品价格不菲,若能够评估和甄别出粘连发生高风险人群,指导合理使用防粘连手段,使患者在合理支出的前提下获益取大化,也是风险评估的价值所在。参考欧洲防粘连妇科专家组(Anti-AdhesionsinGynaecologyExpertPanel,ANGEL)粘连风险评分体系,对患者进行术前及术中粘连风险评分[25](表3-6),术前评分0-36分,术后评分3-31分,根据分值将患者粘连风险分为高、中、低三级。客观统一的评分标准利于医生识别粘连发生高风险患者,并依此指导合适的和合理的防粘连措施,同时还可依据评分对患者进行术前风险告知,减少医疗纠纷的发生。
3.2妇科术后盆腹腔粘连的预防策略
手术医生应当周知术后盆腹腔粘连所带来的可能风险和不良结果。理论上讲,最大限度提高手术技巧,减少术中腹膜损伤,避免腹腔内异物、血凝块残留,减少局部炎症反应程度,抑制凝血级联反应,刺激纤维蛋白溶解以及人为形成医源性防粘连屏障等多种干预措施,有助于预防粘连的形成。粘连的防治策略和原则是既不干扰腹膜的正常愈合过程,又不影响局部免疫功能。除此之外,还要基于患者的医疗保险和经济状况,减少过高的卫生经济负担。
3.2.1手术原则和方法
(1)坚持精细轻柔的手术操作
手术操作中的建议[26,27]:①术中轻柔处理组织,精准使用能量器械;②术野保持湿润,可使用林格氏液内加入IU肝素和类固醇激素;③避免或减少腹腔内的异物污染,改善缝合技巧减少线结暴露;④精细止血;⑤精准组织间隙/腔隙操作;⑥彻底切除全部病变组织,特别是子宫内膜异位症组织;⑦必须切除广泛增厚的粘连组织;⑧精细缝合恢复解剖,修复组织缺损;⑨术毕彻底冲洗盆腹腔积血及组织残存;⑩尽量缩短手术时间。(证据等级C1)
(2)始终执行微创手术理念
由于腹腔镜手术较开腹手术有减少手术创伤的优势,比如更轻柔处理组织、精细止血、持续冲洗、显微操作、术野清晰等,建议子宫切除术尽量选择腹腔镜或阴式手术取代开腹手术[28]。有研究表明腹腔镜手术与开腹手术术后粘连发生率无显著差异,这可能与腹腔镜手术特有的术中CO2气腹影响静脉回流、造成腹腔低温、CO2吸收造成酸中毒/高碳酸血症、组织缺氧及干燥的腹腔内环境有关[29],这一连锁式反应造成组织的氧化应激反应,也会增加粘连的发生,尤其是手术时间较长者。气腹气体的类型、气腹设定压力和流量、气体温度和湿度、手术时长及操作技巧都是腔镜手术后粘连形成的影响因素。
基于腹腔镜手术降低粘连的研究,本共识给出以下建议:①尽量缩短手术时间;②提高手术操作技巧仍然是非常重要的因素;③尽量使用低的气腹压力;④术中对患者进行CO2监测;⑤合理利用冲洗系统对组织降温。如有条件,考虑提高气体湿度、稍微降低气体温度及改变气体成分(加入3%-4%氧气),均有利于减少CO2气腹造成的粘连负面影响[31]。(证据等级C1)
3.2.2术中预防粘连的其他措施
目前临床上可用于预防术后粘连的方法有四种:抗炎药物、腹腔灌注、黏多糖、几丁质类凝胶/液态材料和构建医源性隔离屏障。
(1)非抗生素类抗炎药物
预防手术后粘连的药物包括局部或全身非抗生素类抗炎药物,经验上某些被视为防粘连的药物如地塞米松、异丙嗪等。由于上述药物预防粘连的效果及不良反应存有不少疑问[32],迄今未得到认可(证据等级D2)。
(2)腹腔灌注或腹腔冲洗
本共识不建议单独应用抗生素腹腔灌注用以预防术后粘连的发生。晶体混合液(生理盐水、林格氏液或其中加入肝素、皮质激素),32%右旋糖酐70,用于灌洗腹腔形成“腹腔浴”,据此形成腹膜隔离屏障[33]。晶体液可被腹膜腔快速吸收,速度为30-50ml/h,因此常规应用-ml晶体液灌注,术后24h常可被完全吸收。腹腔镜手术中应用晶体液冲洗,可降低CO2气腹引起的脏层、壁层腹膜干燥引发的肠粘连[34]。但也有研究表明晶体溶液并不能降低术后粘连的发生[35](证据等级C1)。
4%艾考糊精是一种高分子量、α(1,4)键葡萄糖分子聚合物的水溶性电解质溶液,为胶体渗透剂。-ml4%艾考糊精冲洗腹腔,可在腹腔内保留长达3-4天,通过腹膜淋巴回流进入体循环,被α-淀粉酶降解为低分子量的低聚糖,最终经肾脏排出[36]。推荐4%艾考糊精作为妇科手术后粘连预防的辅助措施,用于预防腹腔镜粘连松解术后粘连再行成(证据等级A1)。在欧洲,艾考糊精也被批准用于开腹及腹腔镜手术中预防肠粘连的发生[22,37]。
理论上讲,肝素可以通过抑制凝血级联反应、促进纤溶减少,达到预防术后粘连的作用(证据等级D2)。基于目前唯一发表的临床试验,并不支持肝素溶液冲洗腹腔降低盆腔手术后的腹膜粘连[38]。
(3)黏多糖和几丁质类凝胶/液态材料
透明质酸(hyaluronicacid,HA)是一种由β1,4连接的D-葡萄糖醛酸和β1,3连接的N-乙酰基-D-葡糖胺的重复单元组成的线性天然高分子黏多糖,其无种属差异、免疫原性,可经酶促作用实现生物降解吸收,具有良好的生物相容性和组织黏附性。HA主要通过物理屏障作用将组织分隔,并促进纤维蛋白溶解,刺激间皮细胞增殖,促进创面愈合。HA还可在组织表面起到润滑和保湿的作用,吸收膨胀并压迫出血点进而减少出血和渗出,增强巨噬细胞的吞噬功能,从而减轻瘢痕形成,达到生理性修复的目的[39]。研究显示,不同类型的HA制剂均可有效降低术后粘连的发生,并可避免已有粘连进一步加重[40](证据等级A1)。HA溶液的缺点是在作用部位存留时间较短,对其进行适当交联延长其在体内的存留时间,或许是未来粘连预防的研究方向之一。
羧甲基几丁质是一种生物相容性良好的水溶性生物医学材料,由虾壳提取,具有无毒、无害、无副作用等特点。其在体内可完全自然降解,具有抑制瘢痕中成纤维细胞增殖、分化及分泌,促进表皮细胞和内皮细胞生长,加速伤口愈合,减少胶原形成并促进胶原降解,促进伤口肉芽血液循环的建立,从而减轻组织缺氧,改变伤口及瘢痕组织中免疫细胞的作用,以及抑制创面细菌繁殖,从而减轻感染、加速愈合等多种生物作用,通过多环节作用机制阻断术后粘连的发生[41]。一项多中心、前瞻性、随机对照临床试验[42]表明,羧甲基几丁质不仅能够降低术后粘连的发生率,同时还能减少粘连的范围和程度,并能预防新的粘连形成(证据等级B1)。羧甲基几丁质的缺点是在植入人体后会引起化学性炎症反应,不适宜作为防粘连材料,其在防粘连领域的应用有待更深层次的研究。
(4)防粘连屏障类
防粘连屏障一类的物品,理论上在盆腔器官与手术创面间形成物理性隔绝并发生反应,帮助降低术后粘连的发生。但这类物质在降低远期并发症,不孕、慢性盆腔痛及小肠粘连性梗阻方面未见有宜的确凿数据。美国食品和药品管理局(FDA)批准的防粘连材料有三种,这些用以作为隔离屏障的医用材料,在术后粘连形成、间皮修复的关键时间段(3-5天)可以维持较高的稳定性。
化学改良的透明质酸钠-羧甲基纤维素防粘连膜(Seprafilm):Seprafilm是以HA和羧甲基纤维素(carboxymethylcellulose,CMC)为原料制备的生物吸附膜,经过化学修饰,可延长术后体内存留时间。CMC是一种无毒物质,常用来作为食品、化妆品、医药保健品添加剂。HA/CMC膜是一种可吸收、防粘连薄膜,能够黏附在手术创面,借助物理隔离进而发挥防粘连的作用,该产品隔离效能可持续7天。HA在4周内可从体内完全清除,不影响组织愈合[43](证据等级A1)。Diamond等[44]的前瞻性随机对照、多中心临床研究中,试验组经腹子宫肌瘤剔除术应用HA/CMC膜,其预防粘连效果优于空白对照组。有证据支持HA/CMC膜可降低开腹手术后腹膜中线粘连的机率[45],不过系统综述则认为HA/CMC对于预防子宫肌瘤剔除术后腹腔粘连形成的证据有限[46]。一项大型多中心临床试验[47],将例肠切除手术随机分为2组,一组术中放置HA/CMC膜,另一组不进行防粘连处理,结果显示2组术后小肠梗阻的总体发生率并无显著差异。HA/CMC膜的缺点是应用时可操作性差,容易发生碎裂,腹腔镜手术中应用相对受限,本共识推荐HA/CMC膜适用于开腹手术(证据等级A1)。近几年,改良后的HA/CMC以粉末形式喷洒在微创手术创面,动物实验及临床试验均证实改良后的HA/CMC能有效降低粘连的发生,弥补了其在腹腔镜手术中应用受限的缺点[48]。
氧化再生纤维素防粘连膜(Interceed):氧化再生纤维素是一种可吸收的防粘连膜,黏附性强,无需缝合固定。该材料在体内降解为单糖,并在术后2周完全吸收。多项随机对照临床试验证实,氧化再生纤维素可有效减少术后粘连的形成[49,50]。腹腔镜和开放性腹部手术中应用该产品,可使术后粘连的发生率(新发及复发性粘连)及粘连程度下降50%-60%[46]。年发表的一篇氧化再生纤维素膜预防妇产科手术后粘连的长期卫生经济学研究[51],对子宫肌瘤剔除术和卵巢手术患者随访2年,显示应用氧化再生纤维素膜是极具有成本-效益的干预措施。氧化再生纤维素膜在妇科手术和剖宫产术中,均显示是具有防粘连优势的干预措施(证据等级A1)。此外,氧化再生纤维素膜与肝素具有协同作用,动物实验显示肝素处理过的氧化再生纤维素膜能更有效地降低粘连程度。但迄今为止,鲜有关于应用氧化再生纤维素膜减少术后粘连与生育力保护方面的研究(证据等级C2)。一项小型回顾性研究[52]中,38例不孕症患者接受盆腔手术,氧化再生纤维素膜处理组的术后妊娠率高于未应用防粘连屏障组。美国FDAMAUDE数据库共报告52例与氧化再生纤维素膜有关的不良反应,主要表现为感染、不完全吸收、压迫神经并造成疼痛不适,虽然氧化再生纤维素膜在临床应用已有十多年,但其生物安全性尚需进一步评价。氧化再生纤维素膜用于妇科开腹手术的粘连预防,依据制造商的产品使用说明,残留血液或组织渗血可显著抵消氧化再生纤维素膜的防粘连作用,应用前创面必须彻底止血(证据等级A1)。
膨体聚四氟乙烯(Gore-Tex):膨体聚四氟乙烯是一种无组织反应性、无毒、具有抗血栓作用的永久性、不可吸收薄膜,已用于血管移植数年,因其非免疫原性及非血栓源性,并可抑制细胞的增殖,近年来用于手术粘连的预防[40](证据等级C2)。膨体聚四氟乙烯上有许多微小空隙,可阻止细胞通过和组织的黏附。有研究[53]证实Gore-Tex可有效减少子宫肌瘤切除术后粘连的发生(OR=0.21,95%CI:0.05-0.87)。另一项临床研究[54]显示,在粘连松解术中应用Gore-Tex预防粘连效果优于Interceed(OR=0.16,95%CI:0.03-0.80)。对此结果的解释应当谨慎,因为文章中并未明确在第二次腹腔镜检查时手术医生术前是否已被告知应用的防粘连制剂种类。目前尚未见Gore-Tex在降低小肠梗阻、慢性盆腔痛的发生率及提高妊娠率方面的临床研究。Gore-Tex的缺点在于必须进行缝合固定,尤其在腹腔镜手术中,可能会导致手术时间延长,此外,Gore-Tex无法被机体吸收,术后有可能因指征需要侵袭性操作取出。
04总结与建议术后盆腹腔粘连是手术组织损伤愈合过程中必须经历的病理生理过程。对于妇科手术患者而言,术后盆腹腔粘连可能导致不孕不育、慢性腹痛/盆腔痛、肠梗阻等多种并发症。手术探查能够直观确定粘连部位和粘连程度,仍然是诊断术后粘连的金标准,粘连松解术并不能有效改善粘连相关的慢性疼痛、不孕症以及预防粘连性肠梗阻的发生。对患者进行术前及术中粘连风险评分,根据评分将患者粘连风险分为高、中、低三级。客观统一的评分标准利于医生识别粘连发生高风险患者,并依此指导合适的和合理的防粘连措施,同时还可依据评分对患者进行术前风险告知,减少医疗纠纷的发生。
首先,提倡精细的手术操作,手术中始终贯彻微创手术理念至关重要(证据等级C1)。依据手术前和手术中粘连风险评分,术中应用防粘连屏障类药物(证据等级A1),4%艾考糊精进行腹腔冲洗及透明质酸(证据等A1)、羧甲基几丁质(证据等级B1)等液态材料,可有效阻断或减轻术后粘连的发生,降低粘连相关不良事件发生率及再次手术难度(证据等级A1)。非抗生素类抗炎药物及利用晶体混合液、肝素进行腹腔冲洗(证据等级D2)在预防术后粘连发生中的作用存在较大争议。同时提醒,尽管有防粘连的某些措施,作为手术者一定要摒弃依赖术中建立防粘连屏障弥补手术技术不足的理念。建议利用粘连高危评分方法识别发生粘连的高危患者,针对这类人群选择多种方法相结合的合理手段,降低术后粘连的发生,使患者获益最大化。
本共识旨在为妇科手术防粘连提出指导意见,但并非唯一的实践指南,也不可作为医疗行业标准。在临床实践中需考虑病人的个体需求、所属地的医疗资源以及医疗机构的特殊性,本共识不排除其他干预措施的合理性。
通讯作者:王建六(医院妇产科,北京
44);张师前(医院妇产科,济南
)
执笔作者:徐帅(医院);刘淑娟(医院);王建六(医院);张师前(医院);王建东(首都医科医院);王玉东(上海交通大学附属国际和平妇幼保健院)
参与编写专家(按姓氏汉语拼音排序):蔡红兵(医院);范江涛(广西医院);高景春(大连医院);韩丽萍(医院);贺红英(广西医科医院);孔为民(首都医院);李斌(中医院);李长忠(医院);刘建华(医院);陆安伟(医院);王冬(医院);王世军(医院);王武亮(医院);王小元(山东第一医院);王沂峰(医院);王颖梅(医院);王永军(医院);王悦(医院);熊光武(医院);许天敏(医院);杨英捷(医院);阳志军(广西医院);曾庆东(医院);张燕(医院);朱琳(医院)
向上滑动阅览
参考文献
1SchünemannH,BrozekJ,GuyattG,eds.TheGRADEHandbook.GRADEWorkingGroup;.Availableat:
转载请注明:http://www.jichuc.com/dzws/6067.html